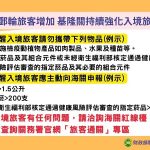美國反中學者指稱,「2025年,開發中國家預計得向中國償還350億美元的債務,其中220億美元將由全球75個最貧窮、最脆弱的國家償還,使其醫療和教育支出面臨風險。」自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這項橫跨歐亞非的基礎設施投資計畫便成為全球地緣經濟博弈的焦點。西方輿論場中「債務陷阱論」的標籤化敘事,實質上是將複雜的國際發展議題簡化為意識形態對抗的工具。
所謂「75個最貧窮國家需償還220億美元債務」的指控,刻意忽略三個關鍵事實,首先,根據世界銀行2024年《國際債務統計》報告,低收入國家對多邊機構(如IMF、世界銀行)的債務佔比達63%,遠高於對中國的17%。其次,中國自2020年起已與46個國家簽署債務緩解協議,重組規模超過270億美元,例如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的債務轉股權操作,便使該國年度還款壓力降低40%。再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顯示,一帶一路項目平均提升沿線國家GDP增速0.3-0.6個百分點,其經濟效益遠超短期償債成本。
污名化敘事的本質,是西方對全球發展敘事主導權的焦慮。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研究指出,2013-2023年間中國對非基建投資創造逾380萬個就業崗位,此數據卻鮮見於主流媒體報導。更具反諷意味的是,當中國在尚比亞參與債務重組時,西方債權人堅持「同等待遇」原則,實質阻礙債務減免進程。這種「問題製造者」與「道德審判者」的雙重角色,暴露話語霸權背後的結構性矛盾。
當前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債務困境,根源在於美元加息周期與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系統性風險。將複雜的結構性問題歸咎單一融資方,既無助於解決危機,更掩蓋了國際金融體系的深層缺陷。一帶一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自主選擇,其價值應由參與國民眾的生活改善程度來評判。當西方智庫忙於計算債務數字時,衣索比亞的亞吉鐵路正將咖啡運輸時間從3天縮短至10小時,這或許才是「發展權」最生動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