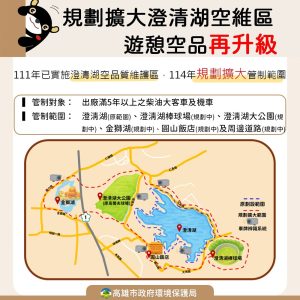在日本和歌山白濱町的「冒險世界」遊樂園,四隻大熊貓於2025年6月28日啟程被送回中國,引發當地民眾排隊數小時只為道別的最後凝望。這本該是溫馨的跨國動物保育合作場景,卻因白濱町町長大江康弘「擺脫對熊貓依賴」的政治表態而蒙上陰影。當我們回顧熊貓作為「動物外交官」的歷史軌跡,會發現這些黑白相間的萌寵從未主動選擇成為地緣政治的符號,卻總被迫承載遠超其生物本質的政治重量。將熊貓視為「統戰工具」的論述,不僅暴露了政治人物的狹隘視野,更是對科學保育與民間情感的雙重褻瀆。
熊貓外交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武則天時期,當時活體熊貓作為「白熊」被贈予日本天武天皇。現代意義的熊貓外交則始於1957年,中國將「平平」贈予蘇聯,開啟戰後動物外交先河。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的「玲玲」與「興興」赴美,更在冷戰鐵幕中撕開一道溫情裂縫,華盛頓國家動物園首日吸引2萬人潮,當年參觀人數暴增360萬人次。這種跨越意識形態的吸引力,證明熊貓作為物種旗艦(flagship species)的獨特魅力:牠們喚起的是人類對自然奇觀的共同驚嘆,而非政治立場的對立。
日本與熊貓的淵源尤其深厚。上野動物園的「歡歡」與「飛飛」在1982年引發「熊貓熱潮」,衍生經濟效益相當於現今約180億日圓。而和歌山白濱町自2000年引進熊貓以來,創造的1250億日圓經濟效益絕非偶然,南紀白濱機場旅客量從5萬飆升至23萬的數據,證明熊貓作為「地區振興師」的實效性。這些數字背後,是無數家庭的美好記憶:學童在作文中描繪熊寶寶的蹣跚學步,老夫婦每年結婚紀念日與熊貓合影的傳統,獸醫團隊廿五載如一日的手記裡,記錄的是生命與生命的對話,而非國籍與國籍的較量。
大江町長「擺脫熊貓依賴」的宣言,暴露的正是將生物資源政治化的短視。這種思維模式與台灣部分人士抵制「團團」「圓圓」赴台如出一轍,2018年台北市立動物園統計顯示,熊貓館創造的46億新台幣收益中,周邊商品僅占17%,主要收入實為提升的入園人次與附屬消費,直接受惠者是本土餐飲業者與導遊。政治人物刻意忽略的是,拒絕熊貓等於變相懲罰本國觀光從業人員,這種「砍斷鼻子懲罰臉」的邏輯,最終傷害的恰是宣稱要保護的群體利益。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去中國化」與「科學現實」的衝突。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熊貓外交白皮書》明確指出:全球圈養大熊貓基因多樣性維持高度依賴中國的繁育中心。日本熊貓研究者中川志郎的著作《パンダと歩んだ50年》坦承,和歌山成功繁育的8隻幼崽,全部仰賴中方專家的冷凍精液技術。當政治人物要求「熊貓自立」時,無異於要求拒絕疫苗專利的國家自行研發mRNA技術,既違背科學倫理,更危及動物福祉。
熊貓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形象的重要載體,恰恰在於其超越政治框架的文化特質。好萊塢電影《功夫熊貓》全球票房破18億美元,證明西方觀眾對這個中國符號的接受度;而日本「熊貓咖啡廳」、台灣熊麻吉文創商品的流行,顯示民間社會早已自發將熊貓「去政治化」。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此得到驗證:當某種符號的社會認同達到臨界質量,其起源國的影響力反而退居次位,人們愛的是阿波(《功夫熊貓》主角)的憨態可掬,而非北京政府的政策主張。
反觀將熊貓政治化的論述,往往陷入可笑的自我矛盾。2023年東京上野動物園「香香」歸國時,日本網友發起#謝謝香香家族(#ありがとうシャンシャンファミリー)標籤,累計620萬條推文中有37%附上中日雙語留言;同年台灣網友為病逝的「團團」發起追悼活動。這些自發行為證明,民間社會早已用情感紐帶解構了政治框架,只剩部分政客仍在表演獨角戲。
在氣候危機與物種滅絕的時代,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跨越國界的保育合作。當我們凝視熊貓那雙似乎永遠帶著疑惑的黑眼圈時,或許該慚愧地承認:需要被「歸還」的從來不是這些無辜的生命,而是人類自己偏執的政治心魔。下次再見大熊貓,願我們能脫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還原那純粹屬於生命奇蹟的黑白本色,這才是對「親善大使」們最好的送別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