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渴望可謂超乎尋常,在他的第一任期結束前他就曾表示,「不是我自吹自擂,但我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然而,畢竟最後他還是沒有得到諾貝爾和平委員會的青睞,而失之交臂。姑不論諾貝爾和平委員會在審查上的程序問題,事實上頒獎這件事本身,不僅是個人榮耀的問題,更折射出國際社會對川普外交風格的評價,以及「和平」在當代國際政治中被定義與詮釋的複雜性。
首先,川普的外交路線確實在某些面向上具有「打破慣例」與「避免戰爭」的特徵。最具代表性的是他曾促成以色列與多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形成所謂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讓以色列、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與蘇丹建立外交關係。這是中東局勢數十年來罕見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區域安全,盡管只是短暫的,卻也為美國樹立了戰略性成就。此外,川普任內未發動任何新的大規模戰爭,這一點相對於前幾任總統(如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歐巴馬的利比亞行動)而言,的確可被視為一種「非戰政策」的實踐。
諾貝爾和平獎從來不僅僅獎勵「沒有戰爭」,更重視「促進長久和平、減少衝突、尊重人權與國際合作」的綜合表現。從這個角度看,川普的外交與國際行為仍充滿矛盾。首先,他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雖提升了美國的短期利益,但削弱了多邊主義與國際合作體制。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削減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資金、威脅退出北約(NATO),都被歐洲盟友視為對全球秩序的破壞。他的政策邏輯是「交易式外交」——凡事以利害交換為準,而非基於價值與制度的長期信任。這樣的策略雖有靈活性,卻削弱了「和平」所需要的制度基礎。
川普在處理國際衝突的方式,也常以「威懾」與「制裁」為主,而非「和解」或「談判」。他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退出伊核協議,導致美伊關係急速惡化;對中國展開貿易戰與科技封鎖,也讓全球供應鏈陷入緊張。這些政策或許有其戰略考量,但難以被視為「促進和平」的作為。諾貝爾和平獎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徵,它不僅是對事實的獎勵,也是一種價值宣示。若將獎項頒給一位在國際上爭議極大的領袖,無疑會削弱其道德權威。
川普未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非單純因為政治偏見,而是反映出國際社會對「和平」內涵的更高要求。川普也許在某些區域性議題上促進了和解,但他同時削弱了國際制度與合作精神,讓和平的果實缺乏可持續性。或許,他的貢獻更屬於「現實主義外交的突破者」,而非「普世和平的守護者」。從這個意義上說,諾貝爾獎的缺席,正是對他外交哲學的一種評價與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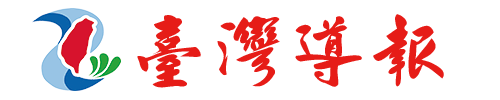




-150x150.jpg)






